特朗普的和談外交真的要奏效了嗎?過去一週眼花繚亂的新聞,難免給人以俄烏和平進程突然加速的印象。8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會見來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圖推進烏克蘭戰爭的和平解決。儘管氣氛融洽,峰會並未達成任何實際成果,特朗普甚至似乎被普京說服,背棄了烏克蘭一向堅持的「先停火再和談」的要求,早前向俄羅斯施壓的和談「最後通牒」也拋諸腦後。
8月18日,忐忑不安之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與英、法、德、意、芬蘭五國首腦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等一衆歐洲領導人訪問華盛頓。出人意料的是,根據《華爾街日報》和POLITICO Europe等多家媒體報道,美歐達成了多項共識:美國可能通過情報、偵查和後勤等間接方式協助歐洲國家為戰後烏克蘭提供「類似北約的」安全保障(NATO-like security guarantees),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被指派負責與各國協調起草有關細節;通過北約和歐洲盟國出資購買的方式,美國將繼續向烏克蘭提供價值多達1000億美元的武器裝備,美國軍工企業還可能入資參股烏克蘭本土的無人機產業;特朗普沒有再施壓烏克蘭,要求後者為換取停火而無條件接受俄羅斯交換領土的提議,尤其是將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兩州漫長堅固的防禦工事群拱手讓敵;澤連斯基亦表示願意在美國斡旋下與普京直接見面談判。
另一邊廂,克里姆林宮與俄羅斯外交部依然對此明確反對,並強調必須解決烏克蘭戰爭的「根源」(root causes),重申徹底否決北約東擴、美國撤出在東歐的軍事存在、乃至烏克蘭「去納粹化」和「去軍事化」——等同強迫其政權更迭和解除武裝——等極度強硬的訴求。俄羅斯的官方表態也僅僅提及提升俄烏雙邊談判的代表級別。不過,特朗普和部分歐洲國家領導人對媒體稱,普京在西方對烏安全保障和與澤連斯基直接會晤等問題上的態度都有所軟化。
但認為迄今已持續三年半之久的俄烏全面戰爭正接近終局,仍為時過早。本文將論證,在各個利益相關方的戰略目標並未根本改變的前提下,造成烏克蘭戰爭爆發和僵持的底層動因仍然存續,導致任何和平安排要麼不可能達成,要麼即使實現也難以持久。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迄今為止反覆不定的調停活動實際上是被各方「操縱」的結果,其實質「成果」僅僅是惡化了烏克蘭戰場的短期形勢,以及損害了美國對外政策尤其安全承諾的中長期信譽。

戰略思維的缺位與美國對外政策的膚淺
對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對歐洲和俄烏戰爭的政策,坊間批評有諸多角度,其中最常見者莫過於指責美國「拉偏架」,在一場是非對錯涇渭分明的戰爭中站到了侵略者一邊。毋庸置疑,本屆特朗普政府中不乏19世紀式孤立主義與強權政治的擁躉,甚至存在一些出於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理由的「親俄派」人士,而特朗普本人也在個人層面對普京有非同尋常的親和感。
但平心而論,正如其他作者在端撰文所分析,特朗普毫不照顧盟友情緒的處事風格,撕破了拜登政府時期在俄烏政策問題上鋪就的一道禮節性帷幕,揭露了一個令人不悅的真相:烏克蘭與西方盟友在這場戰爭中的戰略目標並不完全重合,而是存在深刻分歧。烏克蘭的選擇,是在如下兩種情形之一發生前儘可能避免作出任何實質性讓步:要麼等待俄羅斯被戰爭拖垮、內部崩潰,被迫撤軍接受和平;要麼爭取來自西方最大化的安全保障,例如加入北約。而從西方角度而言,北約或北約式安全保障超出了其國家利益、政治意志和可用資源所能承諾的程度。由於俄羅斯短期內戰略戰敗的可能性渺茫,這就在邏輯上蘊含了烏克蘭僅能通過割讓部分領土、類似蘇芬戰爭後芬蘭的「武裝中立」模式贏得和平,而這是烏克蘭朝野軍民都難以接受的。特朗普政府不再在此問題上虛與委蛇,固然激起完全合理的震驚和道義憤慨,卻也給了烏克蘭和西方國家動力去商討出一個現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然而,特朗普在不經意間將事態推向更務實方向的同時,卻幾乎沒有表現出審慎探討、仔細制定和有效執行一項周密和平計劃的能力和意願。從根本上講,這源自特朗普本人對戰略問題之邏輯的無知,尤其體現在他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簡單化理解。一方面,美國本世紀初兩場對外軍事冒險失敗的歷史令特朗普對戰爭及其災難性後果懷有本能的的厭惡,這部分解釋了他在烏克蘭平民頻遭空襲、加沙平民的飢餓慘狀面前對俄羅斯和以色列態度的變化。但另一方面,或許部分由於其個人經歷,他把長期戰爭視為沒有智慧和能力通過談判交易(deal)解決爭端、做生意致富的「廢物們」(losers)才會陷入的毫無意義的遊戲,而不是「聰明」的行動者會考慮的選項。特朗普對待戰爭的態度,由此以一種詭異的方式與現代和平主義者合流:如果說從和平主義的視角來看,任何戰爭都是不人道的,只要訴諸道義就足以駁倒整飭軍備的理由,遑論參戰;那麼對特朗普而言,任何全面戰爭都是不理性的,只要訴諸(他所理解的)自利就能說服交戰雙方放下武器。克勞塞維茨所謂「戰爭乃政治之延伸」的老生常談,對浮沉政壇十年之久的特朗普來說依然十分陌生。

這並不意味着特朗普在對外動武決策上是一個常規意義上與「鷹派」相對的「鴿派」。畢竟,今年6月他就曾下令出動美軍戰略轟炸機,配合以色列攻擊伊朗的核設施。然而,細看之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恰恰印證了上述論點:這場行動非但沒有在技術上徹底摧毀伊朗核計劃,反而在政治上破壞了伊核協議(JCPOA)或其改良版框架下實現無核化的機會,甚至可能促使德黑蘭政權下決心加速開發核武器;配合以色列近乎尋求伊朗政權更迭的戰爭目標,也不符合美國對中東地區總體穩定的戰略利益。美國從此次軍事行動中唯一收穫的戰果,僅僅是將伊核計劃推遲了幾年。換言之,這種戰略藍圖之缺位的結果,便是對不需要付出政治資本和實質代價的、短期的、戰術性質甚至公關性質之「勝利」的膚淺追求。
在第一屆任期內,特朗普的此一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填滿國防外交部門的職業官僚和政客們的緩衝,使美國的政策在大幅轉變的同時仍維持了相當的穩定和專業性。本屆政府的行政權力大為集中,各個職位的任命都以對特朗普個人的高度忠誠為前提,其缺憾放大到美國外交政策上就變得頗為刺眼。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特朗普在俄烏和談問題上的反覆不定了。正如小布什任內美國駐北約大使、特朗普第一屆任內美國駐烏克蘭特別代表Kurt Volker 所說,他的目標可以簡單概括為:「停火,不管停火線在哪裏,不管誰控制哪片領土;歐洲、北約盟國和烏克蘭自己付錢購買美國軍備;對俄羅斯給予最小限度的必要施壓,爭取普京結束戰爭。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解除制裁,大家都回到過去,正常做生意。」於是,不但特朗普無法理解普京和澤連斯基為何不願在領土等要害問題上讓步,而且經濟制裁與軍事援助作為談判籌碼的功能、屢屢對俄單方面讓步的談判策略之無效也常常遭到忽視。事實上,正如過去幾個月的特朗普無法理解普京根深蒂固的帝國主義執念、無法想象俄羅斯體制下普京決策空間的制約,誤以為只要對後者頻頻擺出示好的姿態就能換取停戰,過去一週的特朗普也同樣因無法釐清烏克蘭安全保障對美國和北約的安全承諾與資源部署有哪些重大影響,而誤以為只要宣布美國僅會間接參與對烏安全保障,就足以將防衛負擔轉移給歐洲國家,在保證戰後持久和平的同時無需承擔美軍介入的風險。

戰略邏輯的枷鎖與持久和平的困難
現實是,導致這場戰爭爆發和持續的各個動因,至今仍沒有重大變化的跡象。
在俄羅斯,俄式法西斯主義的帝國征服戰爭長期以來構成普京政權合法性的基石,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本身就是普京的統治手段。而在所有戰爭中,消滅作為一個西方化的獨立主權國家而存在的烏克蘭身份——普京所謂這場戰爭的「根源」,亦即「基輔新納粹政權」的存在——更是其桂冠。早在2008年的北約布加勒斯特峰會,普京就曾告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烏克蘭甚至都不是個國家,它有一部分領土屬於東歐,但更多部分是我們送給他們的。」如果我們相信今日俄羅斯的統治者對烏克蘭的執着乃出自於意識形態層面的狂熱信念,那麼任何談判和妥協都無濟於事,任何和平協議都不現實,而僅僅是俄軍下一次進攻的前奏。
即使不考慮這一意識形態化的戰略目標,戰爭的走向也將普京推到了一個騎虎難下的位置。歷史中比比皆是源自誤判的戰爭,對己方快速實現戰爭目標的能力之高估便是其中之一,參戰方由此被不情不願地拖入一場無法掙脫的長期戰爭。2022年初的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本意便是通過以政治斬首為目標的特種作戰,迅速在基輔實現政權更迭,從而控制烏克蘭全國。但哪怕在該計劃失敗後,及時收手止損也不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受到此番衝擊的烏克蘭只會加速整軍備戰和向西方靠攏,俄羅斯將面對再也無法挽回的戰略失敗。此外,俄政府的「戰時凱恩斯主義」已成為現下俄羅斯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主要支柱,和平不但會在政治上衝擊普京統治的合法性,還將直接導致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
而在烏克蘭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及,儘管烏軍在戰場上面臨巨大壓力,多數民衆也希望儘快停戰,但在沒有西方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以割讓領土換取停火仍然是政治上的雷區。此種「和平」可能比繼續抗戰還要糟糕:自視被西方拋棄的烏克蘭軍民士氣將徹底瓦解,俄羅斯捲土重來時將輕易得手。這正是歐洲國家幾個月以來力推駐軍烏克蘭以嚇阻俄軍潛在進攻的理由。然而,儘管存在支持其軍事可行性的有力論述,政治上講,除非西方國家能奇蹟般不顧俄羅斯反對強行駐軍,僅僅是在談判中提出該方案就註定被俄方否決,從而無法實現任何停火;任何將烏克蘭納入北約的企圖也會遭遇同樣的困難。

比直接駐軍威懾力稍弱的第二個選項,是由包括美國在內的部分西方盟國共同或單獨向烏克蘭作出專門安全承諾(ad hoc security guarantees),可能呈現為一系列法律效力不等的多邊或雙邊條約、協定、立法或宣言。但任何安全保障的威懾有效性都取決於其底層的利益結構是否堅實。如尼克松所言:「我們的利益必須決定我們的承諾,而不是反過來。」無論奧巴馬、拜登抑或特朗普,美國歷屆政府都反覆表明,為了烏克蘭的領土主權與俄羅斯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不符合美國利益,普京又憑什麼相信一紙文件會改變這一切呢?此外,該安保結構的關鍵,在於與北約和歐盟在組織化程度、適用性等方面作出嚴格區隔(compartmentalisation),以避免將未參與安全承諾的其他北約盟國或歐盟成員國捲入戰爭。但在實踐中,這一區隔完全是人為的。設若俄烏再次開戰,但只有此前作出了安保承諾的部分歐洲國家參戰,這些國家隨之遭到俄軍攻擊,此時其他北約盟國將面臨極端困難的抉擇:如果袖手旁觀,北約第5條的威懾效力將就此崩塌;如果加入戰爭,前述區隔便不復存在,這些國家將被迫在實質上(de facto)捲入自己本不願參與的對烏安全承諾。
但是,正是專門安全保障在風險與收益之間達成的這種表面平衡感,以及「間接協助」所蘊含的虛幻的距離感,誘使特朗普接受了這個看似美國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提議。正如內塔尼亞胡以高超的政治手腕把特朗普捲入對伊朗的戰爭一樣,歐洲國家此番也成功把美國悄悄拉入烏克蘭戰後安全的核心——至少在其意識到問題實質進而反悔之前暫時如此。
駐軍與安全保障之外,僅剩的第三個選項便是烏克蘭割讓領土、採納「芬蘭化」的武裝中立。在這種情形下,烏克蘭唯一的「安全保障」是在西方援助下自身的國防實力。然而,「芬蘭模式」之所以成功,亦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其關鍵之一便是談判雙方的極度靈活:在芬蘭一邊,是無論政治派別,選民對領導人的信任和認可;在蘇聯一邊,是斯大林作為地緣政治現實主義者的理性。在烏克蘭當前的國內政治共識看來,「芬蘭化」與戰敗投降之間只有程度上的差別,這就為無論是澤連斯基還是任何執政者劃出了談判靈活度的邊界條件;另一邊則是懷抱帝國幻夢的普京,又何從妥協呢?

一場操縱特朗普好感的肥皂劇
戰略學者 Edward Luttwak 在極富爭議的經典論文《給戰爭一個機會》(Give War a Chance)中論述道,一場戰爭只有在一方取得決定性勝利、或雙方都徹底精疲力竭時才會轉化為持久的和平。這不但是由於至少有一方的社會經濟結構被破壞到無法再支持戰爭繼續下去,更是因為在政治層面,不斷積累的暴力此時終於徹底「解決」了導致戰爭爆發的根源——或是政治衝突的一方被壓服甚至消滅,或是雙方繼續戰爭的收益無法再為其損害辯護,和平共存變成了更有吸引力的選項。而這就意味着在持久和平的條件尚未成熟之際,通過干預達成的和平儘管用意良好,可能只是一場脆弱的暫時停火,而不是真正的戰略終點。筆者認為,當下的俄烏戰爭尚未逼近這個終點。無論這場戰爭的人道悲劇如何每日殘酷上演,在政治邏輯的枷鎖鬆動解開之前,儘管某種短暫的停火仍可能間或維持,任何持久的和平安排依然十分遙遠。
在此泥潭之中,即使是一位言辭和手腕更圓熟的美國總統也很難扭轉局面;而面對特朗普,有了第一屆任期經驗的各國政府不再驚懼於他的「不可預測」,而是毫不猶豫玩起了操縱其好感的遊戲,以服務於自己的議程和利益。普京無疑是這一遊戲的高手,在過去幾個月來一直尋求將烏克蘭戰爭與美俄關係的其他方面作出區隔,以和談為掩護拖延時間,誘導美國放鬆經濟制裁、減輕國內經濟壓力的同時,繼續在戰場上攫取更多領土。儘管特朗普逐漸意識到對普京示好的姿態沒有換來任何果實,但在某種程度上,普京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美國政府上半年對烏克蘭的支持不力,乃至兩度暫停軍備或情報援助,與後者戰場形勢的惡化不無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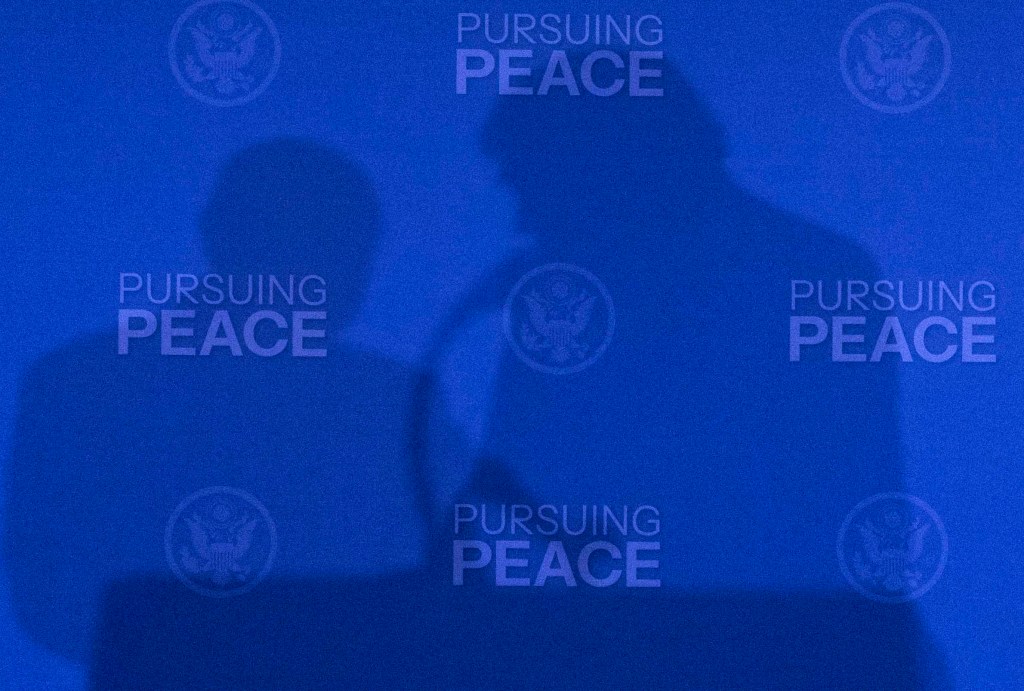
但烏克蘭和歐洲國家也在玩同樣的遊戲。自2月橢圓形辦公室會晤的災難以來,無論是澤連斯基,還是歐盟、北約及其成員國的領導人,都不遺餘力修補與白宮主人的關係,其產物是幾個月來一連串多少有些喜劇色彩的互動:烏克蘭和歐洲國家領導人不斷在公開表態中強調與美國立場完全一致,不斷恭維特朗普的和平倡議,以爭取其向他們的訴求靠攏;後者有時遷就,有時又偏離為他設定好的軌道,5月不了了之的「停火最後通牒」便是一例。澤連斯基從不忘積極響應特朗普對他與普京直接會面和談的號召,突出普京無意和平的形象,以圖離間他與特朗普的關係。如此種種令人哭笑不得的「領袖外交」努力,為媒體貢獻了不計其數的的新聞頭條,卻僅僅是維持了西方脆弱的團結,並未能將俄烏雙方推向和平一步。
這場肥皂劇可能還要播出很長時間。造訪華府和白宮的恭維者絡繹不絕,而取決於一時間哪一方的操縱手腕佔上風,特朗普政府在諸多關鍵問題上的立場仍可能反覆不定。對烏克蘭而言,好消息是歐洲國家承諾的長期軍援會繼續兌現,而特朗普政府也樂意以售武的方式提供軍備。以俄軍推進的速度之緩慢、傷亡之高,僅僅是全面佔領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和赫爾松四州就需要4年之久,要一個世紀才能征服烏克蘭全境,屆時俄軍總傷亡將高達5000萬人。在此之前,俄羅斯經濟可能早已無以為繼:有研究表明,宏觀經濟數據的韌性表象下,是國家指導銀行以低於市場利率給軍工企業的鉅額貸款,而這些隱形債務正成為金融體系內一顆越來越大的定時炸彈。除非和平的希望真正浮現,我們只能合理假定這場戰爭的結局將由軍事力量的對比決定。不幸的是,在轉折點到來之前,烏克蘭戰場絞肉機和平民傷亡的苦難仍不會看到盡頭。





假如要認識普京想法,推薦閱讀《第一人:普京自述》(2002)
諸如這裡:「正如其他作者在端撰文所分析」好想知道是哪篇哈哈
是的,有些資料漏了,已經重加,感謝指正!
原文是否本來包含一些援引資料的連結?看著有些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