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底一位民進黨前黨工在社群網站上公開發文,指出自己於民進黨工作期間遭到外部合作廠商性騷擾,和主管申訴後卻未能受到妥善處置起,MeToo的浪潮似乎終於來到了台灣。
從政治、學術、媒體、文化、演藝到社運界,各個產業幾乎都有女性(及部分男性)現身,說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性騷擾甚至是性侵害經驗。他們多半將這些經歷隱藏在心中多年,因為各種擔心——無人相信、遭遇報復、影響個人工作發展、破壞所在組織或團體的情誼、自己反倒深陷污名——而不敢、不願說出來,直到台灣社會終於隱隱打造出了一種氛圍,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故事值得、應該被訴說,也可能、可以被傾聽、被相信。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受到鼓勵,願意分享自身經驗,我們也才終於得以看見,台灣女性的真實生活樣貌。
他們陳述的方式與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選擇隱去姓名細節,有些人則採以「直球對決」,有些事件較為近期,有些則可稱得上年代久遠。這些事件所涉及的傷害樣態也不盡相同,有些是語言上的性暗示,間或伴隨著威逼和恫嚇,有些則是不恰當、違反當事人意願的肢體接觸。兩造所處的情境,以及雙方關係也都包含了各種異質性。
這些異質性一方面讓我們意識到性別暴力之複雜度,尤其是受害者的樣貌如此多元。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一些提問,有些和性別暴力的基本概念相關,例如類似於「這沒什麼吧?這樣子也算性騷擾?」的評論,另一些則關乎到體制層面的問題,比方說這些不同樣態的性騷擾背後,是否有共同的環境與結構成因?而面對不同樣態、程度的行為,我們應該給予同樣的反應和懲罰嗎?我們又應該如何區分、判定不同事件之間的嚴重性,例如:摸一把就比強吻不嚴重嗎?
在越來越多受害者發聲後,我們也看見兩種新的現象。其中之一是除了受害者本人的陳述以外,有些人則以「旁觀者」的身份出面,表示自己身處的環境也有類似的權勢男性,利用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地位和權力,對身邊的女性進行程度不等的性騷擾、脅迫等。他們或許得知了身邊尚未準備好現身的友人的親身故事,或許是在自己的朋友圈中經常「有所耳聞」,因此在此波MeToo風潮中,決定也做一個揭發者。

另一種現象則更為常見,是擔憂這樣的網路「控訴」風潮難以被證實,最後卻可能造成被控訴者的嚴重後果,如社會性死亡或是被「取消」等。
因為包括性騷擾與性侵害在內的性別暴力經常發生在隱密、私人的環境中,且現場只有兩造雙方,在當下發生的許多事情沒有紀錄,也難以被證實,因而產生了所謂「他說/她說」(he said/she said)的情境,也為這類事件的後續司法路徑與正義之取得增加困難。
近年來隨著女性主義思想逐漸「受歡迎」,女性權益在某些公領域議題(如政治參與)上取得進展之餘,女性也對私領域的性別規範提出挑戰,但同時,也在某些網路男性社群中引發反撲的聲浪。MeToo運動提升了社會大眾對於性別暴力議題的重視,並意識到對女性的性別暴力居然如此普及的同時,這些對「女權高漲」的反彈,結合傳統的強暴迷思,讓女性在提出指控時經常被質疑是不是別有用心——也許是為了錢、也許是為了報復男方,又也許只是因為對性行為反悔了——進而貶低這些受害敘事的真實可靠性。
於是,在越來越多受害經驗被說出來的同時,我們也看見越來越多懷疑與攻擊。其中安柏赫德與強尼戴普的官司可以說是為這樣的趨勢又再次添磚加瓦。赫德與戴普在離婚後互控對方家暴,一度造成強尼戴普疑似因此失去某些工作邀約、遭到好萊塢的「取消」。去年強尼戴普在美國提起訴訟,控告安柏赫德誹謗,最終勝訴。這起案件讓許多人就此主張,MeToo運動非常容易遭有心人士「利用」,最後成為用來誣陷與傷害男性的工具(註1)。
這兩種現象看來服務於相反的政治目的,但他們卻可能對像MeToo這樣一個以受害者主體經驗出發的運動造成同樣的風險。

不被代言的主體
MeToo運動之所以珍貴而重要,是因為這是女性自發並集體性地、用自己的聲音訴說自己的經驗,不經過其他人與性別的代言與詮釋。
很長的一段時間,「你聽說了嗎」是女性社群裡的一個祕密的互助暗號。因為父權社會賦予男性的資格和特權,一方面讓男性對女性的性掠奪得以被合理化,另一方面也讓女性受困於「證詞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這是哲學家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所提出的概念,意指某些人的身分使得他們的說詞變得比較不被信賴。因此,對於女性來說,控訴一個男性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必須付出相當高的成本,展現出特別高的道德水準,才有可能被採信。
與此同時,指控一個男性的同時,女性其實也被迫指控自己。因為性的「賺賠邏輯」、強暴迷思,以及父權社會給予男性的「同理他心」(Himpathy)(註2),當女性控訴一個「壞男人」時,亦等同於將自身放置在「壞女人」的位置上(註3)。於是,在公開控訴成本如此之高、後果又相當危險的情況下,女性往往只能選擇「私下交流」,用隱晦的語言告知彼此:「那裡有危險,你不要去。」
然而,也正是這種壓制女性發言的結構,讓性別暴力難以見光,反而成為一種「奇聞軼事」,是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在此氛圍下,性別暴力問題不被正視,當少數女性決定挺身而出時,他們的經驗也會因為太過「稀有」而使其真實性遭到懷疑。
因此,MeToo運動之所以珍貴而重要,是因為這是女性自發並集體性地、用自己的聲音訴說自己的經驗,不經過其他人與性別的代言與詮釋。透過這樣的發聲,我們得以聽到關於女性受暴的第一手資料,而這正好可以用來駁斥過去每當有女性想要提出控訴時,父權社會總會使用的那套話術:這只是一兩個人、女人被誤導了、這只是道聽塗說。這些大量的第一人稱明白地昭示,這不是一個都市傳說,這是真實到不能再真實的經驗。
這是一個重要的過程,因為奪回話語權的同時,也是女性長出力量的那一刻。女性不再是被消音的那群,而可以用敘事和男性與壓迫者對抗。與此同時,這也是一個主客視角的扭轉,當女性主動發聲,這些敘事所描述的是「女性經歷了什麼」,而不僅僅是「男人做了什麼」,女性得以被放在敘事的中央。
這並不表示,其他人都不能聲援當事人,或在某些時候代為發言,而是我們要記得,運動的主體應該是誰。受害者說出自身經驗的過程,不只讓事件變得真實、讓外人得以理解,更重要的也是為自身培力。因為性別暴力所涉及的從來不只是身體上的傷害,還有信任感與世界觀的破壞,那是行為人透過性的入侵告訴受害者:「我得以違反你的意願、強迫你依循並滿足我的感受、慾望、世界觀。」所以,在訴說並重新詮釋自身經驗時,受害者得以奪回詮釋的權力,拒絕行為人的入侵,大聲主張:「你的慾望並不能凌駕我之上」。
MeToo運動所包含的其實是兩個階段:經驗的呈現與制度的改變,前者涉及的便是從「聽說」到「說」這一個漫長的旅程,以及在其之中,女性作為主體的力量凝聚與展現。如我們擔心有些女性尚未獲得足夠的訴說力量,我們所應該做的也不是主動搶過麥克風幫他們說,而是要盡力打造一個更寬容的訴說環境、給予所有的受害者更多資源與支持,讓所有的經驗都可以被自由與平等地訴說。

不被信賴的主體
一直以來父權社會對於控訴男性的女性都抱持著相當嚴格的標準,受害者們往往必須要表現出格外無暇的道德成績,才有可能被傾聽與相信,不然就會面對各種質疑。
如果說從「聽說」到「說」是一個漫長的旅程,那麼從「說」到「被傾聽」、甚至被相信,則可能更困難重重。如前所說,一直以來父權社會對於控訴男性的女性都抱持著相當嚴格的標準,受害者們往往必須要表現出格外無暇的道德成績、做一個完美的受害者,才有可能被傾聽與相信,不然就會面對各種質疑。
伴隨著MeToo運動和受害者敘事的增加,我們也看到這些質疑仍舊生生不息,但如今經常在比較「進步」的性別觀形塑下,以一種更為中立的樣貌呈現。比方說,擔心可能會有女性以MeToo作為工具,對男性「潑髒水」,以「誣告」的方式試圖造成男性的「社會性死亡」、「取消」,或各種其他「不合比例」的負面後果。
儘管我們的確無法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但筆者認為這種對於「誣告」和「潑髒水」的擔憂,很多時候是一種被過度放大的恐懼,而這種放大來自於一種不合理、不平等分配的同理心。
首先,性騷擾與性暴力的私密性質確實讓其中的真實性難以被確認,但這造成的結果往往是受害者難以透過司法途徑尋求正義。比方說,台灣性侵害案件每年通報數量大約有一萬,但最後定罪的比例不到15%。而在性騷擾部分,根據統計,每年大約有25萬件性騷擾案件,但有八成的受害者選擇不申訴。這表示,在案件本身已經很難成立的情況下,真正的行為人也都鮮少面對法律後果,更別提誣告的成功率。
當然,有人會指出,被錯誤指控的當事人可能根本等不到法律還其清白,光是「社會性死亡」就已經可以帶來足夠嚴重的後果。確實,社群網站創造了一個訴說的空間,也讓人擔心訊息快速傳播的時代裡輿論可能造成的殺傷力。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檢視如今的性別環境,包括許多仍舊不平等的性別規範、在公領域中男女機會的差異,以及當女性成為「性別暴力受害者」後,所經歷的種種——各種質疑、對私生活的攻擊、時間與金錢成本、心理負擔——還有這麼做的成功率,實在很難想像,用MeToo這樣的「殺敵一千、自毀八百」(註4)的手段「潑人髒水」會是一個好主意。
再一次地,這並不是說這類事件不可能發生,但和給予女性經驗的關注相比,每當有女性出面控訴男性暴力時,許多人的關注焦點似乎就會立刻轉移到男性的權益上。在為女性擺脫壓迫、追求正義之前,力求確保男性不要因此太過「不愉快」或受影響。
取消文化和「社會性死亡」的討論亦同。筆者同意,針對取消文化仍有許多值得討論之處,包括「排除」是否等於正義、比例原則,以及資本和國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白話地說:到底是誰在取消誰?)等,然而這類擔心男性提早被取消或是社死的言論中經常忽略一個重要的事實,亦即:早已經有無數女性,因為父權社會中的性別壓迫,以及所遭遇到的各種性別暴力,而提前無聲無息地被取消與排除了。因為這些暴力以及敵意環境,她們或許直接或許間接、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某些機會、失去了某些工作、離開了特定產業,以及曾經可能的大好前途(註5)。
這麼說的並非是要「比慘」,更不是因為女性經歷了苦難,所以男性受點委屈也無所謂。而是想要指出,我們的同理心是否不平等地被分配著,而這個不平等又經常符合了社會中現行的權力位階與資源分配。於是儘管如今女性終於找到了訴說的機會,但我們在給予女性足夠的傾聽和理解之前,卻往往更為重視男性的舒適與穩定。

不被軟弱的運動
MeToo運動儘管涉及的是很多人受傷的經歷,但卻不是一個軟弱的運動,更不是一個宣告女性應該要被照顧的運動。
MeToo運動——或說女性的訴說——所追求的,並不是所有人無條件地隨時隨地和女性站在同一戰線、對女性的說詞毫無懷疑,而是檢討、扭轉過去不甚平等的結構。從父權結構如何合理化對女性之暴力、到女性的證詞為什麼總是不被相信,再到男性的視角經常被視為社會之正統,而女性則被要求要從男性的角度出發,試圖理解男性的動機、感受、想法,進而給予同理、同情和諒解。甚至更進一步來說,父權社會中早已設置了非常多的「工具」(註6),讓男性得以維護自身的利益(且男性團體也經常予以支援),尤其當這些男性已經處於社會上相對有權勢的位置上時,更是如此。
再一次地,這並非表示我們不可以檢討所謂的取消文化。「無罪推定」的原則非常重要,同時我們也應該警醒地對待輿論和正義之間的關係。但是,這些考量並不應該被用來抵銷MeToo運動與各種訴說的正當性,相反地,這反而給予我們更多理由去打造更多、更寬容也更平等的訴說空間,一方面讓各種傷害敘事得以被聽見、理解,另一方面也進而讓各種非典型的性敘事——包括非典型的受害者、享有同樣經驗卻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的人,還有對性互動的不同解讀——都有機會被說出來。透過打造更寬廣的訴說空間與真誠的聆聽,我們首先可以為自己進行一個「敏感度訓練」,在提升對性別暴力問題的理解之餘,也更能夠辨別這些事件背後的同質與異質性。
事實上,如果MeToo可以成為一種惡意指控、潑髒水的工具,原因之一便是父權社會中對於性的特定保守想像,包括所謂的賺賠邏輯,這一方面讓出面指控的女性成為「沒有價值的女人」,也再次透過一種「女人的性很寶貴,應該受到保護」的想像,而將女性弱體化,並且將性別暴力的行為人個別地妖魔化。
然而,MeToo運動儘管涉及的是很多人受傷的經歷,但卻不是一個軟弱的運動,更不是一個宣告女性應該要被照顧的運動。相反地,MeToo的真諦應該是,女人作為一個平等的主體,應該要受到平等的對待,享受免於受到壓迫和剝削的自由。另一方面,MeToo也不是一個打壓男性的運動,在給予個別行為人相應的處置時,更重要的是如何改變體制、檢討當下不合理的性別規範,以及父權社會給予男性的種種資格與特權。
在近日龐大的資訊轟炸下,我們幾乎難免感到焦慮,思索著應該如何回應受害者、又應該如何處置行為人,什麼才是正義?又如何達到修復?作為個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更謹慎但又寬容地面對自己所接受到的資訊,並且以更開放的態度去面對性別議題。更重要的是,儘管面對各個事件,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但與其為個別事件做下判決,我們更應該做的是試圖了解背後的「為什麼」——這指的並不是單純個人層次上的動機,而是這些暴力傷害背後的共同模式,以及是哪樣的權力結構和性別規範,鞏固、強化了這些模式。
終於走進MeToo浪潮的台灣社會,其實如今面對的只是開端。在訴說與傾聽之後,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討論,去思考作為一個集體,我們應該如何回應。
註1:但這麼主張的人往往選擇性地忽略強尼戴普與安柏赫德官司中的其他細節。包括本場官司涉及的是誹謗,而非戴普到底有沒有家暴赫德,法庭中其實也呈現了戴普施暴和意圖施暴之證據,例如他傳給演員保羅貝特尼的簡訊(其中提到他想要燒死赫德)。此外,人們也會忽略其實強尼戴普和安柏赫德在這之前於英國有另一場官司,而戴普於其中敗訴。
註2:這是由《不只是厭女》的作者凱特・曼恩(Kate Manne)所提出的概念,意指父權社會會給予男性較高的同理心,去理解男性的思維、為男性的作為提出解釋,進而原諒他們。
註3:常見的說法包括了:「男人本來不壞,都是被女人帶壞/引誘的」、「好女人為什麼會和壞男人有所牽連」、「一定是做了壞女人做的事情,才會引來壞男人的注意」等等。
註4:這甚至都已經是相對好的結果了,我們更常看到的情況恐怕是「殺敵八百,自毀一生」。
註5:例如她們可能因為出面指控了自己的行為人而被迫離職、失去升遷機會;她們可能不敢說出來自身經驗並滿心恐懼,於是選擇自我退出,不論是疏遠行為人還是放棄本來很好的工作機會;她們可能因此選擇轉職、轉行,希望自己這一輩子都不要再跟這些人有牽連了;她們可能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在自己的訴訟上;她們甚至可能因為受到巨大的創傷,而失去許多能量和自我,最終再也無法成就自己的夢想。
註6:例如利用法律訴訟程序,讓女性必須負起全部的舉證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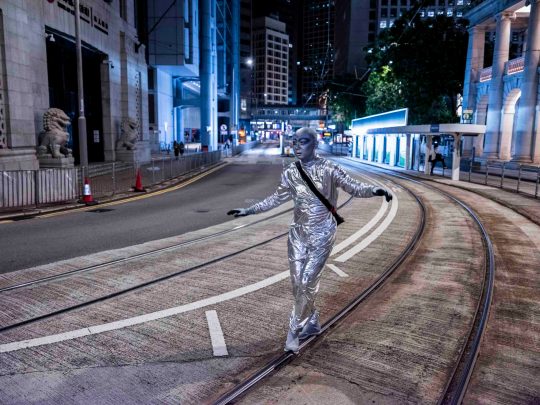


@Hannallin2017 黃致豪之前被捲入性騷擾的醜聞,他說的話大眾,女性不一定願意聽。。。。。。
相關新聞: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103/1346572.htm
雖然底下我已經寫了太長一篇回應…(接下來應該多聽多看少說XD)
不過忽然想到關於很多人擔憂的「被誣告」的議題也許很適合向下面留言中提到的黃致豪律師邀稿(他上過很多節目和訪談,但不確定他有沒有在給媒體供稿?)
我覺得他很適合討論metoo運動中大眾對於「被誣告」的疑慮,是因為他當時在評論強尼與安柏時,有說過,我們不應該因為此案就認為metoo運動是不好的或不需要存在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正視男性家暴受害者的存在 (大意如此),我印象很深刻。
黃致豪律師長年致力於人權、冤獄、司法心理等相關議題,很紅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其中一個主要角色就是以黃致豪律師為原型打造,很希望可以看到他對於metoo運動中大眾對誣告的疑慮,提供一個法律人的視角!!
這篇文章寫得很好,但是沒能打中大眾的情緒,特別是對metoo運動不友好或者不認同者的情緒。我不是在苛責作者,而是這些情緒背後的問題作為metoo運動的限制現在沒人能給出一個答案。對metoo運動不友好或者不認同者而言,他們/她們不會想那麼多概率的問題可能性的問題(正如之前香港鑽石山隨機殺人事件中大眾的心態),他們/她們只會想(萬一)這種事情(被誣告)發生在自己頭上該怎麼辦?這種簡單的同理心促使女性們團結起來推動了metoo運動,自然也會激起其他人對metoo運動的反對。而蠻遺憾的是現在沒有人能找到一個答案去解答。這一點可以看看周作者前些天端上發表的對metoo運動的思考。
大抵同意作者說的,但為什麼一定要把Metoo作為一個女性總是被害方,男性總是加害者的運動來論述?因為這方便套用傳統對父權制度的批評?再者,從同性戀群體的角度來說,這種論述豈不是也是異性戀霸權的展現?就像另兩則留言說的,我以為要打造一個更好的社會,是不要遺漏任何一個受害者。
補充一個先前遺漏的父權體制下我懷疑最可能被消音的性騷擾性侵案件,女對男的性騷擾性侵 (我印象中看過相關法庭判決),我不相信迄今這波台灣metoo運動還沒有相關人出面指證這種事例是因為沒有未爆彈,我更懷疑是因為在父權體制下,男性要出面承認曾經被女性性騷擾趕到不適、甚至曾被性侵,是更加困難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前天周玉蔻戰黃國昌的貼文,我那時候很緊張也很生氣,怕她不負責任的言論會傷害metoo運動 (我認為她的發文是不負責任的言論,她發完數十字的貼文宣稱黃國昌曾經硬上女學生後,黃國昌稱會直接提告,她隔四小時接著說「問一個問題就提告」,然後下一篇貼文戰別人去了…看起來就是毫無根據,純粹是搭metoo順風車做政治鬥爭,而且她戰黃國昌的貼文之間,還插一篇是她和涉嫌偷拍前任私密照的李正皓的訪談,超諷刺…)
還好雖然媒體馬上跟進(那時我也很難過很生氣,網路上串聯這麼多有憑有據的都還沒有人報,周玉蔻幾十字的空穴來風可以馬上上版面QQ),但沒有太多人被帶風向(吧?)
所以我覺得文中說的「許多人就此主張,MeToo運動非常容易遭有心人士「利用」,最後成為用來誣陷與傷害男性的工具」,也是非常需要正視的主張,大家如何一起凝聚共識、討論,在沒有還沒有進法律程序前、在目前法律制度尚有許多不完備之處時,我們更可以相信哪些出面指證(特別是這一波有不只一位第三人出面、和匿名指證(如實踐大學的偷拍案,似乎顯示當時學校並沒擴大調查),哪些值得/需要更多關注,哪些我們要提防可能是有心人士的利用,似乎也是metoo運動中,「網路即為媒體」時的我們所需要邊參與邊修習的媒體識讀課…
另外,關於強尼戴普和安柏赫德之間的糾紛,大眾所能知道事件樣貌是否有助於我們思考metoo運動可能被利用?我還在思考中,也會再回去聽端開麥的「Depp vs Heard,如何影響對#Metoo的思考?」。
當時強尼有公布安柏的一段錄音,大意是說,你可以去告訴大家你被我家暴,沒有人會相信你的,我想這應該是當時法庭戰,輿情逆轉的一大轉折,也有一些媒體和倡議組織,藉機向大眾宣導家暴男性受害者的議題 (按關鍵字搜尋可以看到,當時很多台灣媒體也做很多家暴男性受害者相關報導,包括鏡傳媒、公視等,甚至黃致豪律師當時有上節目分享說,他自己有接過很多被家暴的男性的個案,也知道有些律師會惡意教他們的個案去刺激先生並同時偷錄先生的反映,好提供片面證據,讓太太成功申請到保護令等等,這些討論讓大眾看到家暴的另一個面向,我認為是好事),我覺得就算退一萬步講,肯定強尼戴普和安柏赫德之間的糾紛全然是安柏在利用metoo運動 (我目前偏向認為,雖然法庭戰的部分證實安柏有利用metoo運動之實,也不能證明他們的關係從頭到尾沒有過metoo運動想指證的權勢關係…,特別是開始時很可能是有的…)
偏離我原本想回的東西了,總之我覺得怎樣是「利用」metoo運動,是一件需要深刻討論的事,偏離的部分是想到metoo運動應該可以涵蓋更大範圍、多元面向的權力結構討論,我不相信這會傷害metoo運動或讓metoo運動失焦,反而認為這可以讓我們更身思考父權體制的權力結構的權力結構本身到底是什麼?長什麼樣子?如何不只促使許多男對女的性騷擾性侵,也傷害看似alpha男的男性(因為看起來陽剛,沒有人相信會被家暴)、男對男的性騷擾性侵(我看到網路上其實也有男性響應metoo運動而實名指證被性騷擾,但響應度和關注度似乎相對不大,懷疑男性較不想被安上「性騷擾被害人」的身分,這讓我對第一個出面實名指證的人感到很心疼…,目前在關注的是對#李幼新 #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 的指證)、女對女的性騷擾性侵(台大女舍監對女博生的性騷擾猥褻(按網路消息不確定是否有到性侵程度)的案件)?
很希望每個案子都被接住,當真實案件的樣貌超過當前女權主義的論述所能指認,也許就是需要擴大、更新、深化當前女權論述的時機
Johnny Depp上面五行,打过一个蛇字,女蛇性?
謝謝讀者留言,蛇為多餘字,現已刪除,感謝提醒。
女蛇性?
错别字吧
謝謝讀者留言,現已刪除多餘字,感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