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中,国际肝癌权威、香港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系名誉教授潘冬平之女潘浠淳(Clarisse Poon)卷入“请枪”争议,网民质疑她聘请美国公司“AI Health Studio”(AIHS) 制作药物处方辅助 AI 平台“MediSafe 药倍安心”,以此获得多个由官方或公帑资助机构主办、参与的本地和国际科研奖项。
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数学系二年级生郑曦琳(Hailey Cheng)首先质疑潘的计划的原创性,认为她“请枪”由商业公司代为开发。事态沉寂一个多月后,AIHS 联合创办人 Ahmed Jemaa 于8月4日投下震撼弹,指在2024年3月受潘浠淳母亲、港大医学院前外科学系助理教授彭咏枝付费委托,制作相关平台。
AIHS 在声明中指,彭咏枝委托时未告知作品会被用作参赛,并强调当时客户仅提供初步想法,公司由零开始制作 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最简可行产品),项目开始前没有得到程式码、使用者体验和技术架构方面的资料。又指彭在争议爆发期间,要求他们移除网站上有关 MediSafe 的资料,以及修改字眼,将公司的角色转为商业推广(commercial rollout)。
另一方面,政府相关机构被指牵涉在内及有掩饰的嫌疑。AIHS 声明指事件发酵后,与比赛相关的两个机构——获教育局资助的香港资优教育学苑(学苑),以及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教育城——联络 AIHS。AIHS 向它们提交合约、电邮纪录和付款纪录等与彭咏枝交涉的证明,不过两间机构在7月中回复,指潘浠淳早在2024年提交作品参赛,认为有充分原因相信“作品是原创并且由学生独自创作 ”,又要求 AIHS 对外口径一致,以及将传媒查询转介给他们。AIHS 指两度提供抗辩证据,但未获回复。

Ahmed Jemaa 强调公开事件不是为了邀功,而是不愿意活埋真相,“当机构行事不公、事实被漠视时,我们别无选择。”声明曝光后,舆论快速扩散。《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王丰在 LinkedIn 指有多间政府相关机构和教育团体卷入在内,当中似乎有所隐瞒,“有可能演变成香港多年来最大的教育丑闻。”
两个月以来,事件引发多方争论,包括科研计划的原创性、比赛的公平性,病人私隐是否受保障等等。端传媒整理事件时间线,访问吹哨人郑曦琳、曾参与相关赛事的科研中学生、香港科研专家,并寻求相关单位回应,还原争议来龙去脉,探讨现今科研学生剧烈竞争的状况。

一:潘浠淳是谁,做了什么?MediSafe 争议的来龙去脉是?吹哨人指自己遭受了怎样的攻击和威吓?
潘浠淳是圣保罗男女中学的中四生。她自称研发的 MediSafe 是人工智能网页应用程式,透过与病人资料交叉检查处方,侦测药物处方时的潜在错误,现时网站已无法连上。她今年4月获奖后受访表示,留意到错配药物的新闻,从而受启发研制MediSafe。她又称市面上没有类似项目能够自动比对处方及病人病历,MediSafe 属首创。
她凭 MediSafe 获得多个奖项,包括:
- 2024年10年,学苑与百仁基金等机构组成的“G3 联盟”颁发的“少年创科达人大奖”;
- 2024年11月,“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中的特别嘉许奖、学生创新奖 – 初中、大奖和金奖(由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即数字办举办,教育城是筹办机构之一);
- 2025年4月,以“教育局代表队(中学生)”身分获得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教育局资助学苑,委托新一代文化协会甄选及培训学生参加);
- 2025年学苑“第五届杰出学生奖2025”。
其中,翻查“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的得奖简介,评审均为相关行业的著名人士。学生创新奖评审委员会的主席是香港通讯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陈重义,成员包括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荣休教授钱玉麟、香港电脑教育学会主席和沙田培英中学校长朱嘉添等等,数字办总系统经理(数据平台)翁慧卿亦在名单之内。
当时评审委员会对 MediSafe 的评价为:“从一个优秀的构思开始,基于详尽的资料搜集、对LLM(大型语言模型)、SQL(结构式查询语言,在关联式资料库中储存和处理资讯的程式设计语言)、Vector(向量资料库)的充分了解和深入的医疗知识,善用药物资料库,成功构建出一个非常出色而且易用的系统。”
直至今年6月13日,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数学系二年级生、计算生物学领域的本科生研究员郑曦琳(Hailey Cheng)在 Threads 发布帖文,质疑计划非潘一人完成,引爆 MediSafe 争议。
她附上平台的简介海报,说科研展览很多时候是“富家子弟玩具”,“大家都知中学生根本做不到什么东西出来。”另外她引述潘浠淳今年4月受访表示有76位医生推介 MediSafe ,质疑项目或将病人资料外流至第三方,有私隐疑虑。
潘浠淳随即在 LinkedIn 回应,对郑曦琳的帖文表示“humiliating(侮辱)”,批评是削弱在香港从事 STEM 的女性。帖文之后被删。当时有网民尝试登入 MediSafe ,发现导向 AI Health Studio 网站,当中包括 MediSafe 个案的简介,指明项目客户是潘冬平和胞弟潘冬松所成立的香港肝胆胰及结直肠微创外科中心(Hong Kong Hepatobiliary-Pancreatic & Colorectal Surgery Centre),花8星期制作。
网站亦显示一个更详尽的 MediSafe 版面,罗列制作软件技术、数据来源等,同样列明客户是该外科中心。郑曦琳和网民陆续列出 AIHS 网站的截图、潘浠淳以往访问内容等证据,质疑她聘请公司制作 MediSafe。
热议不断之际,AIHS 网页在6月17日被发现有修改痕迹, MediSafe 个案简介的字眼被改成“协助优化(help optimize)”AI 药物安全软件、“将已有的发明商业化”。
这跟 AIHS 近日声明上的说法吻合,包括彭咏枝在6月16日要求移除 MediSafe 网站上的资讯和调整字眼,将公司角色由从零开发转为商业推广(commercial rollout),公司称有犹豫但依从。声明又透露她表示愿意付费,让 AIHS 继续协助对公众发布讯息。公司指对此感到不安,与彭咏枝断联。
后来,公司发现网站在香港的流量比其他地方多出45倍,才发现有吹哨人公开质疑作为中学生的潘浠淳如何制作如此复杂的产品,并揭发 AIHS 和 MediSafe 的联系。
此外,郑曦琳在事件发酵期间不断于社交平台发帖跟进最新情况,并指曾遭受网上攻击及实体威吓,包括言论攻击她的外貌、双性恋倾向,及以匿名帐号发讯息指会控告她诽谤,并写道:“You’ve no idea whose line you’ve crossed”。
12日早上,她指住所外有一名男子大声呼喊“快啲出嚟”,并疑以不明物体敲打大门,她指已报警及寻求立法会议员意见。19日,她指收到了声称来自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受“郑浠淳女士”委托发出的律师信,要求赔偿港币2500万元。
香港并没有专门保护吹哨人的法律,《信报》引述议员江玉欢指事件涉学术诚信、公帑运用、公平原则等问题,如有人因揭露事件而受到恐吓属违法,政府部门和公帑资助机构应介入处理,并指作品若不光彩地获奖有害香港形象。

二:各涉事的政府部门、比赛主办机构如何回应?最新的资优学苑调查报告出炉,为什么他们认为“药倍安心”符合比赛规则,又如何回应坊间质疑?
事发后,潘浠淳何时联络 AIHS,是否以其制作的项目投奖成为了关键争议之一。
此前,数字办在6月17日曾回复传媒,表示“非常重视”争议,已要求教育城和标准保证小组委员会进行全面调查。其后,新一代文化协会和学苑均指,潘联络美国公司是为了将作品“商业化”,而公司是在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和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后才介入,认为不影响公平性。日内瓦奖评审团则在6月24日表示已审查个案,认为申报资料有效并符合标准,将保留潘的银奖。
但按照 AIHS 近日声明中的说法,该公司在2024年3月获彭咏枝委托,于去年3月11日至2025年6月16日分三个阶段制作、升级和完善 MediSafe,时间早于潘浠淳得奖;同时在过去一年多来,AIHS 断断续续参与 MediSafe 的研发工作。这跟新一代文化协会和学苑的说法有出入。
另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香港联络人杨孟璋近日亦回应传媒查询,指潘参赛时向评委展示她的创意概念,辅以一套自行开发的原型程式来说明,但没有采用任何专业系统做展示,认为她是基于创意和原型而获得银奖。
端传媒去信各涉事单位查询,部分单位于8月12-13日回应。教育局指已要求学苑及香港比赛主办了解,学苑及相关机构正在查证资料,局方会继续与相关单位保持联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下的数字办则回复,教育城的相关调查结果将适时公布。
教育城则指自知悉事件起已立即了解及跟进,包括向涉事人士及机构搜集资料并提问,亦一直以严谨、透明、公平公正的方式积极跟进,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就 AIHS 发表的声明,教育城正要求有关机构及人士提供更多资料,厘清事实。
学苑则于18日以调查报告作回复,报告指“药倍安心”符合比赛规则,同时建议比赛机构持续检视申报机制。
学苑指进行了约两个月的调查,重申该学生早在2024年1月及2月分别向“第26届香港青少年创新科技大赛”及“少年警讯创新科技大赛2023-24”递交作品,提交合共22页的简报,涵盖了问题分析、原理、立论、个案例子、应用程式须具备的功能及建议解决方案等。学苑取得电邮资料,确认该学生于2023年10月已向老师提出其作品概念。
学苑又指,确定相关美国公司及该学生家长,在向两项比赛递交作品后的时间点、即2024年3月开始联系。据了解,双方以有关同学的作品资料,包括设计理念及操作原理等资料为基础,展开商讨工作的方向,对于该公司提到其作品“完全从零开始”(entirely from scratch),学苑认为说法值得商榷;但及后双方交涉的商业活动不属于其调查范围,不宜评论。
对于原创性讨论,学苑表示每个比赛的评审准包括创新性、作品是否具科学性与实用性、参赛者是否具有 ESG 理念、领导才能及创科热诚等。文末建议比赛机构在日后要求参赛者必需留意各样使用人工智能及数据的道德原则,包括需妥善申报任何涉及专业技术及第三方意见的情况。
学苑亦表示,对在过去两个月不同人士遭受攻击等感到痛心,希望各界能停止相关行为。“对于家长或者学生而言,奖项并非最重要,参赛的过程、培养正直及良好的学习心态最为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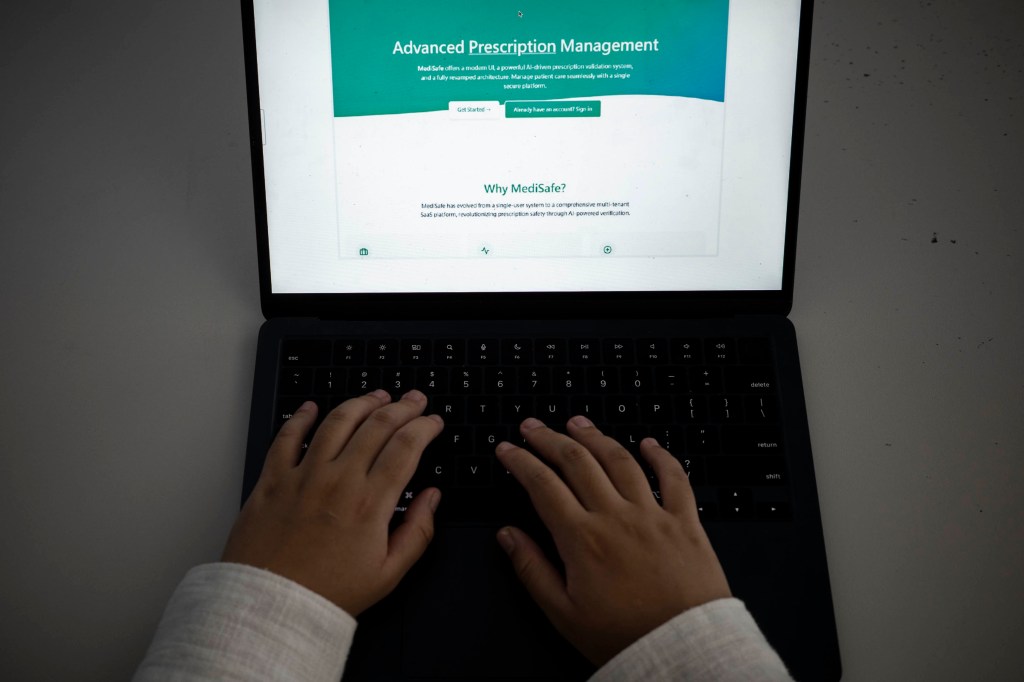
三:MediSafe 是否原创?何为原创?其他科研学生怎样看待今次事件?
MediSafe 是否由潘浠淳原创、何谓“原创”,是事件最大的争议点。
事件中的吹哨者郑曦琳接受端传媒访问,表示最初对 MediSafe 生疑,是因为当中的技术和编程语言“未必是一个中四学生可以做到出来。”她解释,网站分为前端的界面,以及后端的系统——例如是次的药物数据储存和 AI ,而将两者整合,成为可用、甚至商用级的平台,属十分复杂的事。“大学三四年级才会教,又或是资优学生从小到大、编程几年后才学得到。”
她又说,不少编程界人士会在代码托管平台 GitHub 分享代码,但她未见潘浠淳在 GitHub 的帐号和以往的编程纪录,因此觉得事有跷蹊。
端传媒曾联络一名于香港从事 AI 工作的人士,他表示“公开讨论比较敏感”而拒绝受访。
今年3月潘浠淳受访时,表示已为系统申请短期专利。翻查过往的访问,她没有否认独自研发 MediSafe,也没提及“AI Health Studio”跟产品有关连。她在5月接受香港电台访问,主持人指 MediSafe 利用病人病历和公开数据,中学生未必认识或有机会研究。潘浠淳回答说灵感来自医生开错药的新闻,而她曾在于医院和诊所实习,所以思考以 AI 填补漏洞。她表示对 AI“有一定认识”,曾参与 Azure AI 和 AI 及处方药物相关的课程。
主持人笑说潘浠淳“单打独斗”,独自思考程式和搜集资料。潘浠淳说研发过程有困难,她经常需要 debug(除错),又认为自己性格颇独立,提及有两位医生在研发过程中为她解答医学问题。
“在 technical 方面,我觉得有这样能力去 handle 到、解决到问题,就会尽量独立去完成。但当我意识到是 out of my reach……我都要去请教别人,或问别人的 opinion。”潘浠淳当时说。
回看潘浠淳参赛的时间线,按学苑日前说法,她早于2023年10月提出作品概念,又在2024年1月参加“青少年创新科技大赛”,证明项目具原创性。翻查资料,潘浠淳和另一位朱同学在2024年3月于该赛事代表圣保罗男女中学,以 MediSafe 夺得一等奖。该赛事由新一代文化协会主办,学苑协办。
郑曦琳表示不知道潘浠淳有否在2023年制作 MediSafe 平台,但她指潘在2024年获得“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官网的得奖名单显示 MediSafe 的网址—— 指明潘浠淳似乎提交了Al Health Studio 第一期开发的 MVP 参赛。“我们看到一定有外判的元素在里面,不是学生100%原创的作品。”
AIHS 发声明后,郑曦琳曾以潘浠淳于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中所用的海报,询问 Ahmed Jemaa 该作品是否由 AIHS 研发。Ahmed Jemaa 回答指海报所显示的使用者介面(UI)跟 MediSafe 的最新版本相似,颜色、设计和元素亦与公司发布的一致,“似乎是基于我们的工作”。他当时指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从来未联络其公司进行调查。
A 同学是去年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的参赛者之一,他用半年构思和制作产品,以往在不同科研比赛中跟潘浠淳碰过面。他觉得要视乎评审准则决定作品是否合规,不过“有些事可能合规,但不是很道德,你明白吗?”
“评审的决策怎样都会跟 product 的 demo 有关,而这个 demo 不是她(潘浠淳)做的话,对我们不公平,尤其给钱一间大型公司帮你开发,这样更加不公平。”他指坊间不少科研比赛的参赛者是“sell concept”,因为评分准则亦包括汇报和组织能力;现成产品只占其中一部分,但是“当然最后赢的大部分都有喇。”
若然“请枪”事件属实,A 同学认为相关机构应取消奖项。

一名不愿意具名的香港科研专家 B 则向端传媒表示,不同科研计划对原创性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且每一个科研比赛的定位不同,“小学生或中学生比赛,我想一般而言,你不会 expect 他自己做整件事出来。但去到诺贝尔奖,当然需要有很多证明。”
他认为要由比赛主办单位解答:“我们讨论的完成度是去到哪个位置?每个人都有 idea,但是否真的做到?是不是 fraud(欺诈/作弊)呢?比赛机构准则是什么?”
郑曦琳对学苑和教育城的调查结果有保留。她不认同学苑有关“概念原创性”的说法,认为实行方法在比赛中同样重要。“概念固然占一个成份,但怎样去实行这个概念,都是我们作为 science 人会 concern 的……例如我要造一架火箭,但不知道怎样造,只给一个 idea,而这些人(评审)凭著一句 idea 去评分。”
“任何人只要提出想法,就能将整个产品交由第三方完成,这对于真正由学生独立研发、从零开始的参赛者极为不公平。”她指,“有资源聘请外判公司的学生,将比没有资源的学生占尽优势,违背比赛‘公平竞赛’的初衷。”
她以香港青少年创新科技大赛为例,指引列明个人参赛须由单一学生独立完成作品,小组参赛则最多三名学生组成,必须共同完成作品;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则要求有关产品或服务的主要创新、设计及研发,必须来自香港的资源。她认为若参赛作品的技术开发大部分由外判公司完成,已经不再符合比赛的精神与规定。
郑曦琳又指学苑和教育城未有回复 AIHS 有关彭咏枝“请枪”的指控,但让公司将传媒查询转介给它们,做法有如“不希望大家追究”,“会觉得很黑,好像包庇的这些同学的作弊行为……令人觉得比赛就是这么不公平,就是可以益(有利)有钱请枪的学生。”
她希望相关机构能回应大众质疑,澄清事件的始末并让调查透明。在比赛评审制度上,她认为机构应严肃且认真检查作品的原创性,例如评估学生的能力范围,以及审视他们亲自制作的证明。
A 同学说科研圈子对事件的讨论寥寥,他亦专注在自身的研究上,“如果其他参赛者有不诚实的行为,其实我们改变不了什么,可以做的是令到自己的 project 更加好。”他说自己不会“请枪”,有公开项目的程式码,亦不是为争胜而参赛。“就算没有这个比赛,我都会想做这个 project。”
四:科研比赛流程是怎样的?想进入科研界的学生,面对竞争有多大,怎样想自己的出路?
自6月以来,郑曦琳于社交媒体上发布多项帖文狙击潘家,做法备受争议。她向记者解释,这不是私怨,而是想比赛公平进行,以及让外界反思不良的竞争风气,“我希望大家去享受学习、building 的程序(过程),也不要为了入学、为了名誉去参加比赛,制作 APP。”
她说自己对事情反应很大,是因为感同身受。郑曦琳今年初参加一个科学园的比赛,其中一组参赛者的指导顾问为博士生和教授,让她觉得不公。她指该比赛没有规定参赛者列明分工和岗位,“只要那位学生不公开,大家真的不知道有几多成是其他人做,或者自己做。”
她解释,香港的创科比赛通常给予一段时间作研发期,参赛者毋须现场制作产品,而外国较常见的 Hackathon(黑客松) 则是将参赛者聚集起来,规定他们在限时内现场编写程式,“至少看到对手的电脑在做什么”,她觉得这较为公平。
郑曦琳也觉得有评判未必具有技术背景,难以看出作品有否“请枪”。她认为香港比赛著眼在商业价值,外国会看技术,聚焦部分不同,香港有些比赛的评审来自创业投资、银行或学术界,会考虑商业成分、市场定位和项目可行性评分,但将技术部分放轻。
另外是搜集证据的难度。郑曦琳最近在中学的科研比赛中担任评审,参赛者向她汇报和展示海报,并回答问题。她说有项目太复杂,令她很惊喜,估计背后有老师协助,不过她没有证据,亦无从跟进。
“可能大家有种心态,assume 这些比赛全部人都会‘请枪’。”郑曦琳说。“我们肉眼看得出来,但没有实质证据。没有实质证据的话,就不可能令到这些人被取消资格。”

事件的另一争议点,是名校和家长给予学生、子女的资源,与其他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差距。
回想去年的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A 同学说初赛和决赛均以即场汇报形式进行,汇报约长10分钟,评审向他提出问题,包括有没有其他人帮忙、市场上有没有类似的现成产品等。他指比赛竞争很大,几百个项目当中,或只有十多个获奖。
不过在他看来,“请枪”参加科研比赛是少数情况,因为他跟同好言谈之间,能听得出他们有研发产品的能力,而且“请枪很贵。”他评估聘请外国公司研发类似 MediSafe 的项目,花费约为10多万港元。而郑曦琳根据 AIHS 的公开资料推算三个开发阶段:MVP、功能改进和 UI 优化的合计成本至少约为15万港元。
谈到参赛的意义,郑曦琳觉得是兴趣之余,也有不少学生为了堆砌履历,从而在竞争中突围而出。她留意到 AI 行业在国际上很吃香,但香港较少大型科技公司和技术岗位,所以不少学生会考虑到英美发展。而英美学校收生著重课外活动和获奖经验,外国的竞争又比香港大,“无形地令学生去 push 自己、去夺奖。”
她又提到“直升机家长”和“怪兽家长”等,觉得家长和社会对带起不良竞争风气有责任。
A 则觉得,“最重要是我喜欢这件事,所以想挑战,看我有几劲、能力在哪。”建立人际网络、提高产品知名度,以及获奖会有助升学等,都是他参赛的原因。他说亦有参赛者对创科兴趣不大,只为了夺奖入读心仪大学。
他不同意郑曦琳所指的科展很多时是“富家子弟玩具”。访问开初,A 指明:“我的屋企很正常,我家人不懂创科。”他来自非传统名校,学校资源不多,而他在几年前从网上自学 AI,现在正钻研自己的产品,找机会创业。
“对于普通学生来说,这些比赛反而才是机会。我们没有参加这些比赛的话,我们那条路就剩下读书和考 DSE。”他说。
五:MediSafe 还面对哪些医疗伦理,以及版权侵犯争议?
除了非原创的指控外,郑曦琳亦质疑 MediSafe 违犯病人私隐和侵犯版权。
潘浠淳在今年4月的访问谈及,其时已经有医生试用 MediSafe,“为逾千名病人处方药物,至今系统未有出错,准确度达百分之百。”她又指曾向78名医生咨询建议,其中76位推介继续使用 MediSafe,另外在5月访问中,她曾表示让一间肿瘤中心和一间专科诊所的医生试用平台。
而2024年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中,评审亦曾提到 MediSafe 经过“医生和大量临床病患实证,这个系统有效协助医生处方药物”,减轻医疗经济负担,以及对医疗安全起重要作用。
6月19日,潘冬平回复《明报》查询,开腔指潘浠淳作品采用“模拟病人(simulated patients)资料”,又表示十分重视病人私隐,从没采用或向第三方提供任何病人资料。AIHS 8月的声明亦提及系统没有涉及真实病人的数据,而是使用由电脑模拟或演算法产生的合成数据(synthetic data)。
相关机构之一学苑则指,该平台的数据收集符合它们协办的比赛及创科用途,学生在参赛时递交的报告已注明资料仅为“模拟病人”的数据,惟在部分展示品存在令人误会的用词,已提醒留意及改善。又指经该药物数据库澄清,该药物数据可用于非商业用途,未有违反当时的使用条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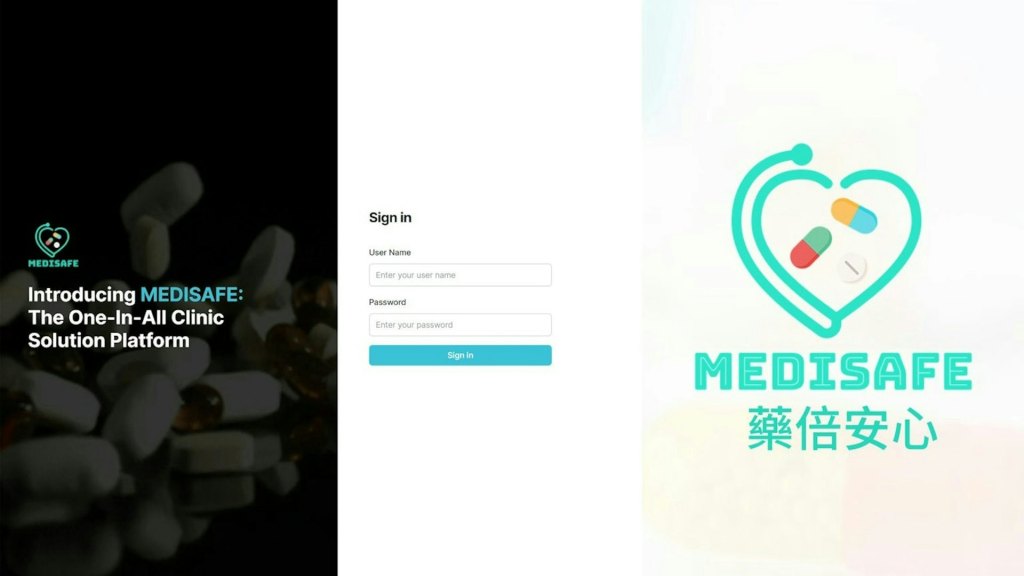
不过,这并未释除郑曦琳的疑虑。她指 AIHS 仅就开发期间使用的数据作出回应,但她针对的是平台开发后,潘浠淳曾称有逾千个病人经 MediSafe 获处方药物——她认为,这些数据有可能在未获病人同意下被储存至系统内,甚至泄漏到海外的伺服器。
郑曦琳又补充,当数据被用于训练或查询模型,将难以被完全清除。她指即使潘以“向量资料库”(Vector database)储存病历,把文字变成特殊数字,而非储存原文,亦不代表安全。这因为在“模型反转攻击(Model Inversion Attack)”中,黑客可以设计问题“试探”AI 模型并猜出原始内容。“即使只留‘数字指纹’,别人仍可能从中拼凑出原本的病历。”她说。
另外, MediSafe 透过 Microsoft Azure Open AI 整合云端资料库的病患和药物资料,郑曦琳亦担心数据会被传送至海外伺服器,失去香港法律的保障。她指希望潘浠淳能厘清有否以真人数据试用 MediSafe。
另外,MediSafe 使用了 Rxlist、Drugs.com 及 WebMD 三大线上药物资料库的资料。郑曦琳质疑这些商业网站没有官方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允许不同的应用程式、系统等之间共享资讯与功能)供人合法提取数据,潘浠淳或以“数据抓取”(俗称“爬虫”)大规模复制资料到 MediSafe 的数据库内,有侵犯版权的隐患。
就此,她和网民向 Drugs.com 查询事件,在今年6月得到电邮回复。Drugs.com 表示没有授权让 MediSafe 复制、散布和使用网页上的资料,而在未经授权下使用网页的内容会构成侵犯版权和违反使用条款。平台又指已向 MediSafe 发信要求将有关内容移除。
“这的确是一个很常见的挑战。”接受端传媒采访的科研专家 B 表示,本地大学也正努力解决科研过程中出现的私隐、版权问题,“人工智能就是数据训练,如何去保障?Federal learning (联盟式学习)是其中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技术还有改进空间,大学亦正研究利用科技梳理版权使用的追溯等等。
他又指,目前许多大公司会提醒员工不要将数据轻易放上公开 AI 平台,也开始会以企业人工智能,即私有化 AI 模型确保数据在独立的环境中使用,确保其私隐性。“AI 私隐是一件颇费力的事。”被问到学生科研项目是否有足够资源做到相关保障程度,他指未能论断,要看看个别人士是不是相关方面的专家。
郑曦琳对记者表示,最近收到的恐吓很频密,感到很大压力,“其实我更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这些事件会削弱公众对教育和科研的信任。”她计划未来转到美国升学,继续做 AI 医疗相关的研究和发展初创,“因为在那边的科研环境、学术风气、创业机会都更加开放和多元。”
“我相信这才是对社会真正有价值的方向,而恐吓只会令我更确信这条路要坚持走下去。”她说。
(端传媒曾去信潘浠淳 LinkedIn 上显示的电邮地址、经香港肝癌及肠胃癌基金会向潘冬平、彭咏枝寻求回应,并两度致电至潘冬平成立的香港肝胆胰及结直肠微创外科中心,截稿前未获回复。)
(尊重受访者意愿,A 及 B 均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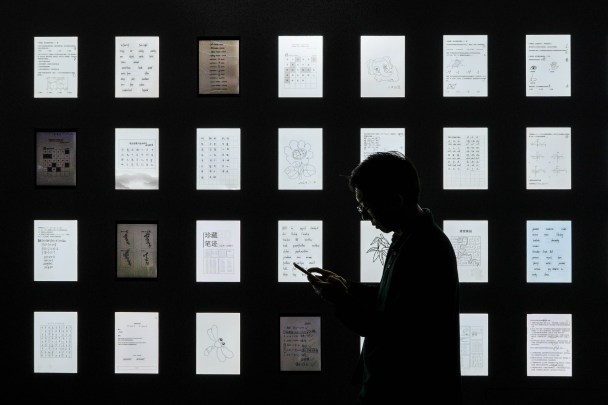

身有屎仲咁理直氣壯我第一次見
黃子華:Buffet 不妨食過份,出貓唔好太高分
多謝端,多謝鄭曦琳。